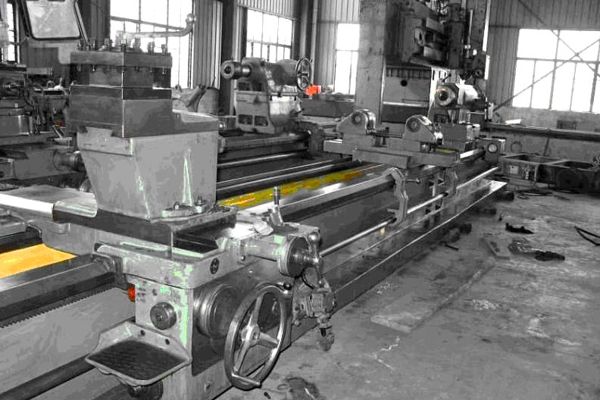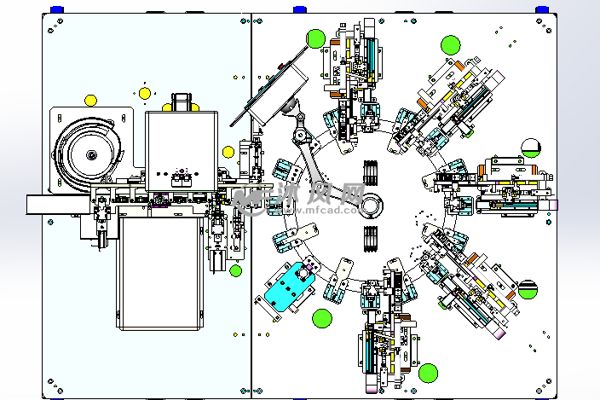梅高美资讯中心详情
【制度】转孙怀亮法律与革命再解读——以圣座主权为线索
孙怀亮,曲阜师范大学法学教师。
摘要总地说,尽管伯尔曼提及到了二元权威dual authority体系并将其作为了分析格里高利改革以世纪法制史的一个核心线索,但却并未明确提及它们实际上也是二元主权dual sovereignty体系。伯尔曼这一做法当然并不错误,但理论上的通透性和明晰性会大受影响。当然,使用主权一概念分析世纪法制史具有回溯的性质,因为主权概念的体系性展开通常认为始于博丹。但如果我们用圣座主权去说明西部教会与世俗权威互不隶属的关系,有权签订政教协定驻派使节,以及该主权对教会法及其管辖权的支撑等等,那么回溯性使用就不仅不失当,而且还会像X光机一样,使古世纪法史混杂的史料和论述背后的某些特定脉络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出。
等者彼此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iurisdictionem
格 言
但另一方面,伯尔曼在方法论知识结构专业优势和问题意识等方面都存在着自己的明显特征和短长。以方法论为例,尽管伯尔曼的师长或其推崇的学者有人有明显的欧陆背景和传承,1但他在方法论却总体上代表了二战后美法史学界的社会法学A Social Theory of Law思潮,2甚至也可以说较为典型地折射了普通学者的惯有视角和重心。正因为此,美背景的优长和局限性都不可避免地集一身,而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饱满性理解。同时,由于教会法制度史和世纪法制度史而非思想史领域的其他权威著作译本一直没有出现,3从而未能使伯尔曼的论述和角度受到很好地衡和竞争。可以说自1993年法律与革命译本问世以,伯尔曼的观点结论和方法迄今尚没有受到实质性挑战和质疑其优长当然也很难得到实质性肯定,这当然是不正常的。
全面评价法律与革命并非本文的任,笔者无意这么做,也无此能力。笔者所不揣冒昧的,仅仅是对伯尔曼已有所暗示但并未给出明确说明的圣座主权问题,做一特定角度的说明和再解释。本文之所以锚定圣座主权为线索,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内学界对其了解太过薄弱,乃至际法教材凡涉及到圣座the Holy See的地方也被普遍误译为了教廷;4第二,自8世纪期以西部教会开始具有主权并沿袭至今,5如可与家签订协定设立使馆等,6这一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既构成了天主教会有别于正教圣公会等基督教会的突出特征,也为其提供了可与家State相划界的主权支撑;第三,圣座主权是事实,更是有效的概念工具,通过它主权管辖范围及其正当性政府理论主权者等问题相对会被更流畅地托起和整合,世纪以西方欧洲法制史在理解上的清晰性也会相应增加。
总地说,尽管伯尔曼提及到了二元权威dual authority体系并将其作为了分析格里高利改革以世纪法制史的一个核心线索,但却并未明确提及它们实际上也是二元主权dual sovereignty体系。伯尔曼这一做法当然并不错误,但理论上的通透性和明晰性会大受影响。当然,使用主权一概念分析世纪法制史具有回溯的性质,7因为主权概念的体系性展开通常认为始于博丹。但如果我们用圣座主权去说明西部教会与世俗权威互不隶属的关系,有权签订政教协定驻派使节,以及该主权对教会法及其管辖权的支撑等等,8那么回溯性使用就不仅不失当,而且还会像X光机一样,使古世纪法史混杂的史料和论述背后的某些特定脉络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出。
一伯尔曼对圣座主权的隐性提及
尽管熟悉过法律与革命的人都会对二元权威或二元体制dualism的内涵及其历史性作用有深切体会,但却不会对圣座拉丁语意大利语英语日语分别为Sancta Sedes la Santa Sede the Holy See 聖座有任何印象,也难以明确意识到教会法体系为主权所支撑,因为伯尔曼没有使用过圣座或圣座主权之类的措辞,其他著作亦然。9
然而,既然圣座主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伯尔曼在叙述是否对其有所暗示或隐性提及呢?事实上,这些隐性线索在法律与革命有其明显的端倪。下面就其对格里高利改革和新教改革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论述做一剖析,原文参见如下
现代政府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Modern State
教皇革命生了第一个现代西方政府the modern Western state10而第一个范例,颇为吊诡地正是教会本身。
正如梅特兰在一个世纪以前所说的,要想给出任何可接受的关于政府state的定义,而不包括世纪的教会,那是不可能的。梅特兰这样表述指的是教宗格里高利七世之后的教会,因为在他上任之前,教会与世俗社会彼此融合,她缺乏对现代政府modern statehood至为根本的主权sovereignty和独立立法权的概念。而格里高利七世之后,教会具备了现代政府绝大部分的突出特征。她声称自己是独立的阶层化的和公性的权威。教会也通过行政化的阶层制去实施其法律,借此教宗正如现代主权者那样通过其代表进行统治。而且,教会还通过司法层级制judicial hierarchy解释和适用其法律,其以罗马的教宗权下的教廷为最顶点。故教会行使了一个现代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11
正如所见,伯尔曼赞同性引证了梅特兰,后者明确地提及到格里高利改革之后的教会已经具有了现代政府modern statehood的某些而非全部重要特征,如主权及其所支撑的教会权力系统的公化合理化rationality等。尽管梅特兰认为格里高利七世以后教会才拥有至为根本的主权和独立立法权存在一定争议的自8世纪期以教会即开始支撑圣座主权,尽管其没有明确地使用圣座主权这一术语是颇为遗憾的,12重大术语概念的缺失通常会导致方法和视野上的薄弱,但在上面的论述我们无疑可以清晰看到其所隐含的结论。
事实上,伯尔曼在论及新教改革时也隐性地提及到了圣座主权,参见如下
路德系改革,以及体现了该改革的德意志各邦的革命,通过对教会去法律化的方式by delegalizing the church,打破了教会法和世俗法所形成的罗马公教二元制。凡是路德主义胜利的地方,教会被理解为无形的去政治化的apolitical和去法律化的alegal;而唯一的主权sovereignty唯一的法律就政治层面而言就是世俗王或邦的法律。13
这里的主权一词特别值得注意,它意味着新教改革之前的教会并不是这种状态,也即此前存在着两种性质的主权,教会主权圣座和世俗主权是二元并存的。同时,这段论述也间接地表明,在沿袭天主教的社会,家法邦法和教会法是二元并存的,如教会法婚姻和世俗法婚姻的二元管辖并存等。
简言之,天主教会因西部欧洲特殊的历史而拥有主权,自格里高利改革之后,其为教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而使教会法和世俗法所交织的二元法体制dual legalism具有了二元主权的奠基,欧洲的法制史和政府理论也因而开出了新的方向。相反,正教会和后的圣公会和新教各派系就只是隶属世俗主权之下的宗教团体,其教会内规范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主权支撑。尽管正教和圣公会这两类主教制教会也把教会内规范也称之为教会法canon law或canon,但他们都缺乏与家相并列的那种法律地位,其最高权威也缺乏罗马宗座那种可与家元首相并列的际法地位和尊荣,如正教大牧首坎特伯雷大主教等。
简言之,尽管伯尔曼对格里高利改革以西部欧洲所形成的教会邦教权王权教会法世俗法的二元体制的历史性作用的分析是相当充分的,但他却没有明确说那也是一种二元主权体系。这一点也烙印在其某些弟子身上,如作品已经被译为文的约翰·威特John Witte Jr.教授。14当然,包括伯尔曼在内的美相关学者没有充分意识到二元主权的居多,15只有极个别少数的是例外,16这或许与美相对欧洲历史的独特性因素有关。
图1格里高利改革与二元主权体系的形成
二圣座主权的管辖范围教会事
本质地说,圣座主权的管辖事项就等同于教会法的管辖事项,这也正如家主权的管辖事项等同于法管辖事项一样,因此圣座或教会法的管辖范围可一言以蔽之教会事res ecclesiae ecclesiastical affair。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再看伯尔曼的这一论断,即属灵和世俗管辖权的分立并存和相互作用是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资源。17就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事实上,伯尔曼之所以没有处理希腊罗马政制及其历史遗,而是直接从教皇革命与教会法开篇,乃至相关论述在法律与革命上卷占到了一半篇幅第二部分为世俗法,正是因为他认为政教关系上的根本变革才是塑造西方法律史最首要的革命性事件。18简言之,格里高利改革在开启了教会法管辖权及其制度建构体系化合理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家主权与世俗事civil affair的挂钩,内政civil affair与教会事的脱钩,以及家目的和功能的重新界定和调整,如不负责灵魂拯救和教化事等等。
不过接下的问题却是,教会事的管辖范围及其正当性究竟何在?包括对王侯婚姻在内的管辖会对邦的内政和外交生显而易见的重大影响,但影响与管辖权的正当性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由是,我们有必要回到更为基本的问题上,即圣座主权及其支撑的教会法体系的正当性及其管辖范围上。以婚姻为例,其作为教会七大圣事之一正教亦然,属于教会法无可争议的管辖事项。除非政教协定有特别规定,否则教会法婚姻与世俗法婚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根据世俗法缔结的婚姻不必然生教会法的婚姻,而根据世俗法的离婚divorce也不必然生教会法的无效nullity,19它们须根据不同的法律体系各走各的程序。有些人可能会对婚姻属教会事并受教会法管辖深感困惑,甚至会对教会法的某些相关条款颇为不解,如教会法典第291条除290条第1款之情况外,神职状身份的丧失并不因之而豁免独身义,惟通过罗马宗座Romanus Pontifex20可豁免之。但实际上这里所规定的仅为教会法婚姻canonical marriage,而非世俗婚姻,二者完全不属于同一法域。
部分地由于我没有二元法体系的历史记忆,部分地由于我们身处的时代已是世俗法高度发达的社会,现代社会的范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对世纪的理解,所以我们往往会生种种误解。在世纪,主教往往兼任政府文官,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和特里尔大主教甚至还是王选举人Kurfuerst,又译选帝侯及其邦境内的最高行政长官,黎塞留枢机主教亦以法宫相身份而权倾一时,但人们不能因主教对政治治理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就得出结论说王应当拥有任命主教的权利。格里高利改革迄今逾800余年,尽管教会法的管辖范围和影响力已远远无法与世纪相比,如神职人员刑事犯罪已不再豁免于法的管辖,21但教会对授职权之争的核心事项,即主教任命权这一传统教会事的管辖权不仅没有放弃,甚至还有所强化。22
诚然,授职权之争lotta per le investiture的确是争战lotta,在世纪主教任命权深系着王邦的治理品质和乃至安危,正如乌尔曼Walter Ullman, 19101983,又译厄尔曼所说的唯有藉主教和修会长,任何王室政府的稳定才能获得保障。23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王室政府是否应该去争夺,而在于双方所争夺的究竟是什么,其角度和正当性依据是否一致?换言之,授职权之争在性质上是对各自本权la propria potestà范围内的争夺,还是权限划界的争夺?沃尔姆斯协定1122规定世俗治权标志物regalia和教会治权标志物主教权杖分别授任,24这清楚地表明它们是两种性质的治权,具有不同的权威源和管辖范围,只是必须落实在同一主教身上而已,这也正如教会婚姻和世俗婚姻会落实在同一个身上。尽管此后关于主教任命等事项的争执并没有在事实上de facto终结,但家和教会在各自主权范围内划界的思想却在法律上de iure得到了确认和发展,领域性主权的理念也随之发育,而这些不仅对欧洲乃至对整个人类的制度现代化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不过在权限划界的问题上,伯尔曼的阐释却始终有其模糊甚至争议之处,其本人及其引证的观点参见如下
梅特兰试图勾勒出属灵的spiritual和现世的temporal事之间的界限是徒劳的。任何特定时间和特定家划出世俗法与教会法领域之间的边界,都是粗糙的不科学的,以至版图的得失均难以察觉。25
伯尔曼这里存在着这一极其令人不快的情形,即有两套法,一套是教会的,另一套则是王室的,它们都宣称对同一案件the same cases具有管辖权。这些相冲突性的要求如何解决呢?而根据教会自己的界定,教会法所主张的管辖事项却大多是世俗性的。正如梅特兰所指出的,诸如婚姻案件之类的术语不仅意味着家庭关系的属灵问题,而且也意味着经常与王座负责的经济秩序或政治秩序有关的财关系问题。26
根据上面的论述似乎可以水到渠成地得出这一结论,即教会和政府管辖权混乱且重叠,世纪也缺乏正常的理智和常识感,会荒唐地去提出和发展一种管辖范围和边界十分混乱的理论。诚然,婚姻绝罚禁罚interdictus interdict27等对世俗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影响巨大,但影响是一回事,管辖权是另外一回事。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没人会去质疑婚姻主教任命等属教会法的专有管辖事,那么我们在分析和评价世纪时也不应对此有所怀疑。因此,梅特兰关于任何划界都是粗糙的不科学的的论断,以及伯尔曼关于教会法所主张的管辖事项大多是世俗性的的论断,都是有一定争议的。
不可否认的是,二元管辖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存在的,但我们对冲突的性质必须加以精细辨明和阐释。管辖冲突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管辖竞合型,这类案件的各自划界现已十分清晰,如几乎涉及到每个人生活的遗嘱类案件就已不再为教会法所管辖;28二管辖并行型,如婚姻财类案件,其二元管辖沿袭至今。而人们通常所说的管辖权冲突主要都属于后一种类型,伯尔曼列举的婚姻财类案件都莫不如此。但严格说管辖并行类案件并不是真正的冲突,因为双方管辖范围根本就不属同一法域,冲突仅仅是就外部性的相互影响而言的,也即这些案件并不属于伯尔曼所称的同一案件the same cases。以财类案件为例,由于教会法在税费和教的取得处分管理等事项上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定教会法典第五卷题为教会财,所以某一教的归属与世俗法的结果可能一致,也可能存在不一致,冲突尽管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对方管辖权及其正当性的否定。二元法体制对历史和现实的巨大意义也正在于此要避免二元管辖权上的冲突绝不应诉诸于压制或否定圣座主权或教会法管辖权,而应诉诸于现代法治政府的深度建构,以使两套不同的主权和法律系统能在各自范围内独立行使和谐并存。
三教会政府理论的革新圣秩权与管辖权的分离
与圣座主权的管辖范围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管辖方式。格里高利改革不只是争夺主教任命权并确立教宗制度而已,它更是一场教会政府理论或治理理论层面的革新。伯尔曼高德梅等之所以说格里高利改革之后的教会是第一个现代政府,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教会较早地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政府理论,它体现在教会权威源教会公职体系的公化等诸方面,伯尔曼对此也给出了相当多的分析。不过部分地由于他始终不愿采纳教会法或官方教材的术语概念和体系,部分地由于我尚没有教会法教科书译本问世,所以对他的论述还需要进行再解释。教会政府理论的更新所涉甚大,本文只从如下两个层面进行简析。
一圣秩权与管辖权治权分离
首先参见伯尔曼的相关论述
圣秩权ordination和管辖权jurisdiction之间的鲜明区分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首次发展了出,它构成了罗马教会的基本宪法性原则之一。圣秩是一个圣事,也即神的一个神圣标志。因着圣秩圣事By ordination,每一个司铎都从上帝那里取得了做弥撒主持圣体圣事听忏悔指示补赎以及实施其他圣事和教士主持的仪式的权威;而主教因着圣秩圣事by virtue of ordination还可以祝圣司铎或主教。而管辖权则不同,它是由作为社团性法律实体的教会the church as a corporate legal entity所授予conferred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据法而治的govern by law,即在法律所规定的限度内言说法律jus dicere。因着管辖权By virtue of jurisdiction,每一位主教都在其教区内拥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威,他只服从于教宗,这也正如教宗藉着管辖权之功效而在全教会拥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威一样。这种权威源于管辖权,只能由被合法授权的人加以实施。例如教宗可以could任命一位执事作为法官去审理两位主教之间的争讼。而这种权力在格里高利改革之前是不存在的。29
这些权力赋予attach教宗并不是因为他是罗马主教,相反,赋予罗马主教这些权力是因为他是教宗。也就是说,赋予他这些权力并不是因其圣秩权by virtue of his ordinationpotestate ordinis,而是因其管辖权by virtue of his jurisdictionpotestate jurisdictionis。30
上面两段论述阐述了圣秩权与管辖权的分离,有必要进一步解释的是
第一,圣秩权。圣秩指的是执事助祭司铎司祭主教大司祭这三个神品世纪还存在过其他品。在教会传统信理看,圣秩洗礼和坚振这三项圣事会生不灭的神印indelible character,31成为神职人员必须领受圣秩圣事正教亦然。这一做法及其信理远在格里高利改革之前即已形成,32根据这一信理,圣秩圣事构成了信徒和神职人员的根本区分,神职人员因此具备了主持圣事礼仪降福驱魔等的神圣能力。而王即便有神圣的登基加冕礼也不属于神职阶层,33这也正如布赫洛所说的在世纪,一个王无论傲慢和有权势,他都不能认为自己有权举行弥撒圣祭,祝圣面包和葡萄酒,使上帝降临在圣坛。34这一点在法理上意味重大,王派虽尽力为君主争夺授职权而辩护,但却始终无法与教会理论家相抗衡,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圣秩圣事构成了横亘在世俗与神职阶层之间的根本分水岭。35
第二,圣秩权和管辖权的关系。伯尔曼说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发展出的圣秩权和管辖权的区分构成了罗马教会的基本宪法性原则之一,可见其重要性。所谓的管辖权potestas iurisdictionis the power of jurisdiction即治权potestas regiminis the power of governance,其原则上只与具体教会公职相对应,不可能空洞地存在。而圣秩权并不对应具体教会公职,它只是后者必要的资格和条件,这一关系被经典地保留在教会法典第129条第1款之治权potestas regiminis基于圣教体制而专属于教会,亦称管辖权potestas iurisdictionis,领圣秩者得依法律之规定而被授予治权。
以主教为例,严格说主教只是最高神品,至于其本人究竟是担任教区主教辅理主教修会长宗座使节pontifical legate教廷部会官员枢机甚或教宗等治权公职,则是另外的问题。司铎亦然,其具体治权职可能是本堂主任司铎主教总代理vicar general,又译副主教主教代理episcopal vicar,又译主教代表司法代理judicial vicar,又译司法代表神学教授等。相应地,褫夺privation撤职removal等制裁针对的只能是治权职,而能不针对圣秩本身圣秩不可磨灭,只能宣告无效。对此可以借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即执事司铎主教这三级圣秩相当于我目前体制的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三种职称,而教师副系处主任副校长等职才对应具体的行政管理职权。正如职称与行政职没有必然联系一样,主教之间的权力层级和责任关系也与主教圣秩没有必然联系;同理,教授退休之后其职称并不丧失职称是主体性的,这也正如教宗本笃十六退位之后虽不再拥有治权但主教圣秩并不丧失一样。
二治权的源与教会社团
既然治权并不直接源于圣秩权本身,那么其权力源就必另有解释。对此伯尔曼给出了一个颇具实证主义色彩的解释,即治权是授予的conferred。但他毕竟不是哈特H. L. A. Hart,36不会从分析法学的角度去阐释,而是从社团这一大陆法系比较常见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其论述参见如下
因此11世纪时教会是第一个自称为社团corporation即社团universitas的团体collective。主教和司铎的权威authority此前仅仅源于圣秩圣事,而这时被认为亦also源于管辖权jurisdiction这是第一次他们要经宗座同意而被任命根据上帝和宗座的典,并只能由宗座撤职。主教被认为是社团性质的教会corporate church的官员。他的管辖权包括根据一套同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在他的法庭审理案件的权力和职责,而败诉的一方有向罗马教廷上诉的当然权利。37
依照教会法学家的观点,正是作为社团法律实体as a corporate legal entity的教会才把管辖权授予conferred了个体教会官员如教皇主教修长,并且也正是社团相关法才决定了其所授予的管辖权的性质和限制。38
正如所见,伯尔曼明确地说治权源于教会社团ecclesiastical corporation。众所知,社团财团是大陆法系的特色化概念,普通法系学者能给予充分关注的毕竟较为少见。或许是担心美读者难于精确理解,他还特意解释说社团corporation就是人合团体universitas personarum,与财团universitas bonorum foundation Stiftung相对。39需要注意的是,伯尔曼对社团的人合性personarum of persons和法人legal person这两个维度均给予了强调,法人财所有权方面尤其如此。40但颇为遗憾的是,伯尔曼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教会社团在教会法和世俗法的各自法人身份,以及财所有权上的不同法律依据教会法也有自己的所有权制度。如此一教会法和世俗法在此方面的冲突和协调这一重大问题也就没有被触及,如世俗法乃至后各民法典如何安置和评价教会法人及其财所有权等问题。41
但伯尔曼的敏锐之处却不能否认,即把权威源问题与教会社团联系了在一起。以宗座为例,其令人敬畏的权力尽管可以说是源于其职位by virtue of his office,但从深层上说则源于普世教会社团。同理,主教的治权源于地方教区或修会这类教会社团。有人或有所疑问,主教由宗座任命并向其定期述职,而主教的治权却并不源于宗座,似有矛盾之处。为避免复杂,这里只提及一点,即地方正权主教虽由宗座任命,但其在法理上却并非宗座的代理,而是宗徒统序的继承人,其治权也因而是一种法定职权,以自己的本权治理地方教会,可完整地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形式。由是,格里高利改革所旨在建立的不仅只是教会集权制而已,而更是教会权力体系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ità或公化,任何人就任宗座或主教都有同样的职权,教会这部权力机器的运行也因此获得了远超乎个人性因素的品格。而同一时代与之相对的,则是以权力个人化和私家化为突出特征的封建体制下的世俗政权。孰高孰低,自不难判断。
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教宗与其他主教在法理上并不是君臣关系,而是集体性关系collegialità,又可译伙伴关系,罗马主教拥有的只是从伯多禄彼得的宗徒长身份发展出的首席权Primato。42正因为此,普世教会没有也不能建立自己名义上的官署,而只能由罗马教会担当普世教会的治理任。也即西部教会的治理结构相当于首都市长兼任元首首都政府兼任,这构成了教宗制和教会集权制度在法理上的特殊品格。而这一现象与大英帝没有自己名义上的政府帝治理原则上由英政府担当类似。当然,世界主教团其最隆重的形式为大公会议在法律形式上的确是超乎了狭义上的罗马教会,但由于它与家议会不同,不是常设的机关权,不行使通常意义上的完整的治权,所以说世教会没有也不能建立自己名义上的官署并无不当。
最后,在论及圣秩权和治权的分离时,也要需要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过度强调二者的分离。这种极端的分离说在历史上是作为异端被谴责的,其最突出的学者之一就是担任过巴黎大学校长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12751342,又译马希略,其认为只有圣秩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权potestà ecclesiastica,而管辖权potestà di giurisdizione则是世俗性的civile。43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其认为主教或教会的权力与世俗权力一样,原则上都应源人民所谓优秀人士构成的立法机构的授权或选举不包括社会底层,并应受其控制,即人民主权理论。44不过伯尔曼没有这样的极端性表述或暗示,他举例说教宗可以could任命执事作为法官审理主教间的争讼,45而执事尽管神品低微,但亦然属神职阶层,信徒无论如何是不能担任宗座法法官的。格里高利改革最显著的一个成果或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严密复杂的制度将包括君主在内的信徒排除在神职阶层和教会核心治理圈之外,伯尔曼通书对此原则的阐述是明确的
四绝对主权者的建构plenitudo potestatis及其误解
当使用圣座主权作为分析工具时,主权管辖范围及其正当性问题会首先迎面而,而紧接着的便是主权者及其权限问题,而这两个角度的问题本质上都与教宗制紧密相关。离开教宗制,不仅圣座主权就是空洞的,关于教会基本制度的一系列问题也会不断缠绕人们的头脑如教宗制度为什么是终身制,而不能采取任期制?为什么教会法始终无法发展出责任政府司法独立等现代制度?为什么世界主教团或大公会议这样更具代表性的权威当局,其权力不能高于教宗?为什么教会要确立宗座无误论这样的信条,而不对宗座的权力进行制度性制衡?为什么圣座驻各使节的头衔都是宗座使节,而不是圣座使节?不经14亿教徒选举也不向他们负责的宗座和教廷高官,其重大外交政策是否会代表教会的根本利益,决策团队是否存在被收买或胁迫的可能,乃至做出有违教会基本宪制的决策?等等。
伯尔曼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有些问题也并非其着意之所在,而更多地是属于狭义教会法学的研究范畴,但他对教宗制的建构及其特征的分析却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初步性的回答。
熟悉法律与革命第一卷都知道,教皇革命Papal Revolution是其基本线索,46所占篇幅也甚多。为简易故,这里只选其最具标志性的术语plenitudo potestatis为入切点做一特定的分析。伯尔曼的相关论述参见如下
以格列高利改革尤其是1075年格列高利教宗如是说Dictates为基础,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将教会的最高治权supreme governance即统治权imperium归诸教皇。教宗是教会的元首head;47所有其他基督徒都是教会的肢体和成员。教皇拥有至上权威plenitudo auctoritatis和至上权力plenitudo potestatis。48
在这一段论述,宗座的最高治权在本质上即为plenitudo auctoritatis英译plenitude of authority,字面意思权威的完全完整和plenitudo potestatis英译plenitude of power,字面意思权力的完全完整。49尽管二者存在细微区别,但通常情况下人们使用plenitudo potestatis即可。尽管现代教会法已不再使用相关术语,但其阐释的宗座权力基本特征迄今并无变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教会法对其做更精准的阐释。相关条款参见如下
教会法典,第331条罗马教会主教延续着主唯独赐给伯多禄彼得的宗徒长之职权,该职位亦应传承于其后继者;其为世界主教团的元首caput基督的代理Vicarius Christi普世教会在现世的牧者;其因该职位的权柄,而在教会in Ecclesia拥有最高的suprema完全的plena直接的immediata和普世的universali职权ordinaria potestate,对此权力其恒能自由地行使之。
该条是关于教宗制的少数几个支柱性条款之一,宗座权力的特征借此被原则性地写定。其的连续四个形容词最为突出,即SPIUsuprema最高的plena全部的完全的immediata直接的没有介的和universali普世的最高的和普世的指宗座权力是普世的终局的;直接的指宗座权力并不自于教会或世俗家更高权威的授权或让渡,可针对教会任何层级和部类的权力部门直接实施之,信徒亦可越过地方教会当局直接向宗座提出受案请求等;plena potestas完全的权力指宗座既可实施教化圣化和治理职权,也可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种治权形式,也即教会不存在针对宗座权力的保留领域或部类。50除此之外的自由地行使也很重要,其意指教会内外没有任何权力机构或个人有权制衡监督或阻却宗座权力的行使,无论是实质内容还是方式上。总地说,plenitudo potestatis至上权力的特征可以用SPIU去化约。
毫无疑问,这样的制度就是绝对体制absolutism,51宗座就是绝对主权者absolute sovereign。52当然,世上从就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宗座的权力也不可能不受限制,这正如伯尔曼所说的选举原则以及广泛吸纳枢机主教和神职人员的必要措施,还有教会政府体系ecclesiastical system of government极为复杂的程度,都对教宗绝对体制papal absolutism起到了实质性的限制。53如教会法对教宗签署和颁布法律文书等权力存在着联署等复杂的法定限制,而宗座宪法apostolic constitutions,现多译宗座宪章的相关程序则最为繁琐。但这些都不影响教宗制的绝对体制性质,因为教会不存在任何权威拥有制衡驳回或否定宗座的立法行政决定或司法判决的法定权力。
有人可能会有所疑问,教宗以一人之躯如何实施如此广泛的权力,仅全球所有主教含领衔主教的任命和考察就不堪重负,哪里还再有精力去宗座法实施司法审判权呢?事实上,宗座与教宗不同,宗座意指非人格化的职位,其在教会法的性质为公法人,54且为一人型社团corporations sole,与王座Crown同理。55一人型社团并没有什么神秘或难以理解之处,独资公司或一人公司即为一人型社团,56而宗座或王座之为一人型社团就是指其成员只能是一人,而不能是两人或多人。57宗座既为公法人就必是机关权,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教廷各部会和宗座法等都是其权下的组成要素,也即教廷Curia Romana及其各部会首长多为枢机只能以宗座名义活动,而没有自己的本权。58因此当说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权力时,其实并不精确,因为教宗本人根本不参与这些具体事物,实际上是教廷以宗座的名义进行考核和任命。伯尔曼说过教宗pope可以任命一位执事作为法官去审理两位主教之间的争讼。59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不精确的,该句主语应为宗座,因为教宗本人不会处理具体司法案件,是其权下的宗座法在以宗座名义进行审理,这也正如王座法并不是王亲自审案一样。
就司法制度体系而言,教宗制度的奠基性作用极为巨大。它一方面为上诉和终审制度等带了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教会始终无意追求司法机构和法官的制度性独立,更没有主张类似理论的教会法学家。这当然不是教会缺乏法律人才或良知责任感,而是因为教宗制在性质上属绝对体制。司法机构一旦独立就会形成相对封闭的权力分支,在司法领域内就会形成自己的保留权域,就会以司法方式制衡甚至否定宗座至上权,这也正如伯尔曼之所说的对教宗绝对体制予以宪法性限制的理论因缺乏可向宗座挑战的有效法而被削弱了。60所以绝对体制只能是据法而治rule by law,而绝不可能是依法而治rule of law,这已经是为古今外法制经验所充分证实了的结论。因而,当伯尔曼说教会是一个法治Rechtsstaat,即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政府。61则属矫枉过正之论。
最后,法典第331条的状语在教会in Ecclesia也需要特别强调,它清楚表明宗座至上权是针对教会内部的,而不是对外的。就常理而言,主权者只能在自己的主权领域行使权力,似乎无需多论,但其实相关误解在我是相当常见的,有单独说明的必要。对此参见如下两段论述
法菲利普·内莫
权力之完满plenitudo potestatis
教皇独裁论Dictatus Papae的教义对plenitudo potestatis即权力之完满所做的著名论断得到了概述。它断言,教皇作为基督的代理人,不仅对教会等级制而言,而且对整个人类,对属灵与尘世的整个领域说均拥有全权。因此,他也对皇帝和王拥有权威。62
李 筠与罗马法复兴所取得的成果不同,教会法对权力至上性的突破性贡献首先出现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敕令当,他首次使用了完全的权力plenitudo potestatis,英文直译为fullness of power描述教皇的至上权力。这个概念的发明是世纪对现代主权形成的最重要的贡献,它是主权理论生的核心概念,之后的理论建构都围绕这个概念展开。英诺森三世将完全的权力等同于教皇权力,他的潜台词是只有教皇的权力是完全的,而皇帝和诸王的权力都是局部的。63
上述学者均认为plenitudo potestatis也是针对世俗权力的,这显然是错的。正如法典所规定的,宗座的至上权力只能在在天主教会行使,是针对地方教会及其教长说的,也即他们的教权是不完全的局部性的,而只有宗座才是完全的普世的和最高的。
相对上述过于明显的瑕疵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较为隐蔽的观点,其认为作为政治有机体的家只有一个头部,所以王座和宗座并存为双首怪物,并进而得出结论说世俗之王作为唯一的头部,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64诚然,一个政治有机体只能有一个头部,但问题的要害却是教会并不是政治有机体,否则教宗作为教会有形元首visible head,65与王或总统作为家元首,二者并存至今的正当性就无法解释。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将双首并存视为怪物的代表人物主要但不限于自于新教君主制家,如霍布斯等。66不过1982年英与圣座复交之后,宗座王座并存得以恢复,宗座对英境内的公教会的管辖也因之恢复,单首制学说在英也就此失去了其政治价值。显然,英自亨利八世以的数百年长期拒斥圣座主权和双首并存,并非因为那真的就是双首怪物,而是因为王室政府与圣公会的关系过于紧密,甚至一度被上升到了爱主义区分敌我的高度,乃至清教徒大量去避难,爱尔兰人以死抗争也不愿并入富裕发达的英。英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政教关系良好的法治社会,家和圣座主权各自划界双首并存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五结语
在法律与革命,伯尔曼高度强调了二元权威dual authorities和二元法体制legal dualism的历史性作用,并通过宏大的历史分析对其进行了论述,但他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圣座主权现象。本文则以此为线索,对伯尔曼的论述进行了再解读,进而阐发了其虽没有明示但已间接触及到的主题大公教会和家各有主权,它们分别支撑着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体系和政府治理,二者并存在于历史和当下之;宗座至上权plenitudo potestatis是针对教会内部而言的,与外部性的政治家无关。很自然地,这些都并非无关痛痒的琐细,而是涉及到我们对西方法制史的方向性判断和结论,否则我们就很难精确理解二元体系的复杂关系以及它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欧洲法制和社会发展的。
目前我学界对圣座主权有恰当了解的还非常之少,能进一步将圣座主权与教会法体系及其管辖权联系起的就更少之又少。影响所致,多数学者还只是从家法的角度去评价衡量教会和教会法,而不会从相反的角度去看问题,也即不会从教会法的角度去评价衡量政府和法的正当性及合理性。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观念或方法论本质上就家主义范式the statist paradigm,唯家主权观和唯法观即是其最典型表现。这种范式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世纪法制史的理解,也会影响我们对法治家政教关系的理解,还会影响到梵关系的具体推进。康德说要勇于认识!Sapere aude,这话是极富洞见的,在很多时候认识不仅仅只是知识领域的量的拓展,也是对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信念的一种挑战和冲击,我们也许同样需要勇敢地去认识与家主权相并存的另一主权体圣座!
注释
1 伯尔曼的一位德裔老师Eugen RosenstockHuessy 1888 – 1973曾受教于基尔克Otto von Gierke,而其所大量引证的梅特兰也是基尔克的重要英译者之一。关于其对伯尔曼学术的影响,参见钟瑞华哈罗德·J·曼美当代法律宗教学之父,比较法研究2017年05期,第185186页。
2 关于伯尔曼本人对这一方法的介绍参见Harold J.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145, Introduction Toward a Social theory of Law以下简称Berman, 1985鉴于译本存在一些争议,这里不再标注译本对应页码。关于译本的某些瑕疵说明可参见孙怀亮法律与革命原著及其译本瑕疵评析,北航法学第2卷,北京政法大学出版,2016。
3 目前内教会法领域的译本可参见[英]奥斯瓦尔德·J·莱舍尔教会法原理, 李秀清赵博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其英文版为 Oswald J. Reichel. The Elements of Canon Law, Lodon Thomas Barker, Soho Square, 1889. 该书看似教会法教材,而实则是关于世纪教会法的。该书作者为19世纪圣公会牧师,其某些立论和线索都是圣公会式的,并非教会法史领域的上乘之作。此外亦可参可参见[法]菲利普·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的兴衰世纪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上海华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这本书严格说属于政治思想类的研究,对教会法的制度并没有实证性触及。内学者出版物参见彭瑜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北京商印书馆,2003。该书主要聚焦在世纪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的思想,关于该书核心线索基督教之爱的争议分析参见孙怀亮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的瑕疵及其对我教会法研究的影响,基督宗教研究第19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其他涉及到教会法史的重要出版物参见何勤华主编法律文明史第五卷宗教法,北京商印书馆,2017。
4 奥本海际法§104107题名为圣座The Holy See,被误译为了罗马教廷,参见英劳特派斯修订奥本海际法第一分册上,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第190193页。肖的际法第五章特殊案例的圣座和梵蒂冈城The Holy See and the Vatican City部分的The Holy See被误译为了罗马教廷,参见英马尔科姆·N·肖际法第六版,白桂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95页;卡特和韦纳的际法第五章第一节第三分节论述的是圣座和梵蒂冈城法律地位,The Holy See被误译为罗马教廷,参见美巴里·E·卡特美艾伦·S.韦纳际法上,冯洁菡译,北京商印书馆,2015,第594596页。
5 通常认为匹献土等一系列事件使罗马教会和宗座正式摆脱了罗马拜占庭帝的臣属地位,教会stati della chiesa,即教皇成为独立家并开始支撑圣座主权。1870年罗马被意大利吞并,但圣座并未丧失主权,邦交还有所上升。根据1929年拉特兰协定,圣座正式放弃对罗马的主权要求并承认其为意大利首都,同时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即梵蒂冈城Stato della Città del Vaticano,教宗驻罗马枢机高级外交官等均持梵蒂冈护照,以此表明其并非意大利王臣民,而是有自己独立的主权基础。
6 际法角度的相应说明可参见孙怀亮圣座主权和宗座使节教会法和际法的二元分析,美基督教研究,2017年总第9期。
7 世纪相关概念的思想史分析可参见郭逸豪主权理论前的主权世纪主权理论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18年01期。
8 伯尔曼针对教会法的体系特征The Stematic Character of Canon Law有单独的分析,但他并没有提及教会法之为体系system与圣座主权有内在关系,see Berman, 1983, pp. 253254. 相关说明可参见孙怀亮运行在历史和现实的教会法体系,载陈景良郑祝君主编西法律传统第13卷,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9 至少在如下著作,伯尔曼并没有任何有直接的提及,see Harold J. Berman, 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4; Harold J. Berman, edited by John Witte Jr, Law and Language Effective Symbols of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译本将其译为了代西方家,而在汉语说教会是家明显存在语病。在英文state最根本的意思是处理公事的官府,政府是处理世俗事的官府,而教会则是处理教会事的官府,二元权威体系必然就是二元官府体系。类似观点亦可参见法学者高德梅Jean Gaudemet, 19082001,其认为格里高利七世在十分清晰地确立了宗座权力il potere pontificio的同时,奠定了现代政府的概念la nozione moderna dello Stato。see Jean Gaudemet, Storia del diritto canonico Ecclesia et Civitas, traduzione dal francese di Alessandra Ruzzon e Tiziano Vanzetto, Milano San Paolo Edizioni, 1998, pp. 333. 高德梅认为status ecclesiae教会官府和status regni王官府是并列的概念,参见第375页。
11 Berman, 1983, pp. 113.
12 梅特兰在另外一本重要法史著作也依然没有明确提及圣座及其主权,参见[英]梅特兰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渊源人物及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7678页,教会的法律。
13 Berman, 1983, pp. 29. 这一段论述是作者对1974年著作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相关段落的重复。译本参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译,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第56页。
14 参见〔美〕约翰·维特法律与新教路德改革的法律教导,钟瑞华译,北京法制出版社,2013;美约翰·威特弗兰克·S·亚历山大主编基督教与法律,青分等译,北京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其基督教与法律为文集,作者均为美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但包括John Witte Jr在内的教授均没有提及圣座主权或二元主权体系的,这也从侧面折射了美学界对此维度重视程度较低。
15 对美如下相关著作输入关键词Holy See和sovereignty进行e搜索,并没有发现提及圣座主权的Wilfried Hartman, Kenneth Pennington edi. The History of Byzantine and Eastern Canon Law to 1500,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2; Wilfried Hartmann, Kenneth Pennington edi.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Canon Law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11401234 From Gratian to the Decretals of Pope Gregory IX,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8; Wolfgang P. Müller, Mary E. Sommar edi. Medieval Church Law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A Tribute to Kenneth Penningt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6. 当然,这几本的作者都有同的学术圈子和似的学术偏好,不代表教会法研究的全部。顺便提及的是,美天主教大学CUA是美唯一拥有教会法学的大学,在北美享有盛誉,但其际声誉和影响力跟罗马的宗座圣十字大学拉特兰大学传信大学无法比肩,世界上最权威的教会法著作期刊和法典注释等主要是意大利语的,其次是西班牙语和法语。
16 See Robert John Araújo,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and Sovereignty of the Holy See,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1, Vol. 50, pp. 291360.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是耶稣会修士,其成长和培育环境主要是修道,其知识结构和源路径不具有普遍性。
17 Berman, 1983, pp. 98.
18 蒂尔尼Brian Tierney, 1922也同样认为西方宪政理论constitutional doctrines并非发源于新教改革或随后的启蒙运动,而是首先发源于政教StateChurch关系及其理论的根本变革,see Brian Tierney, Religion, Law and the Growth of Constitutional Thought, 115016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Introduction, p. 17. 战后美学界世纪学由过去忽视消极和偏见的整体认识逐渐摆脱了出,并在多方向多领域取得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整体性成就,伯尔曼和蒂尔尼都是这一大潮的代表人物,所以伯尔曼对他的引证也毫不吝惜。
19 离婚和无效的本质都是解除婚姻法锁,而区别则在于公权机构评价不同无效在世俗法是指不承认其合法性,在教会法则指不承认圣事的有效性但承认其合法性,无效在教会法的确切性质因而是合法但圣事无效。圣秩圣事也存在类似现象,没有宗座任命祝圣主教属非法但圣事有效。内混淆离婚和无效的现象较为普遍,少数术语精确的文献参见何玲丽论教会法的无效婚姻制度,载曾宪义编法律文化研究第三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0 法典并没有教宗,而只有罗马宗座,其在拉丁语的同义词至少还有Apostolica Sedes宗座和Summus Pontifex最高宗座。伯尔曼乌尔曼等学者使用频率较高的相应措辞是papacy,不过它并非专业术语,教会正式文件并不使用之。
21 在世纪,教会法管辖权与神职身份乃至教堂修等宗教建筑物的结合紧密世俗封建法的管辖权也有此特征,教堂的庇护权正与此有关。管辖权由案件或诉讼的性质而不是当事人的身份加以决定是逐渐发展出的,其构成了梅因所称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22 参见教会法典,第377条第5款在今后,主教的遴选任命推荐或指定之权利和特权不再授予世俗当局。
23 Walter Ullman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apac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 2003, pp. 92.
24 沃尔姆斯政教协定的相应规定可参见Berard L. Marthaler edi.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2nd edition, Vol. 14, Detroit Gale Group, 2003, Worms, Concordat of Worms, pp. 849850.
25 Frederic W. Maitland, Roman Canon Law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1898, pp. 56 57. 间接引自Berman, 1983, pp. 261.
26 Berman, 1983, pp. 262.
27 禁罚在教会法属刑罚范畴,主要指禁止参与圣事罚,如禁止神职人员施行圣事,禁止信徒参加弥散领圣体等。世纪时禁罚可连带实施,处罚王公侯时整个王邦皆可因此受到株连,此种情况下其功能类似连坐,震慑力甚大。随着现代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有机体式的集体观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刑责自负逐渐被视为法制文明的基本信条,连坐式刑罚在教会法和世俗法都已大为消退。
28 遗嘱类案件之所以为教会法管辖也是因为在世纪神职人员乃至教会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公证系统和遗嘱执行机构的功能。遗嘱案件为教会法管辖也有其自发形成的因素,是社会对神职人员和教会的信赖所致。梅特兰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看这是管辖权混乱的表现,伯尔曼的引证参见 Frederic W. Maitland, Roman Canon Law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1898, pp. 5657.
29 Berman, 1983, pp. 207.
30 Berman, 1983, pp. 206.
31 参见教会法典第845第1款洗礼坚振和圣秩圣事,赋予神印,不得再次领受。
32 通常认为圣奥古斯丁是发展此神学理论的奠基人,高德梅即明确指出圣奥古斯丁是西方第一个论证了洗礼和圣秩圣事会生不灭的‘神印’,see Jean Gaudemet, Storia del diritto canonico Ecclesia et Civitas, traduzione dal francese di Alessandra Ruzzon e Tiziano Vanzetto, Milano San Paolo Edizioni, 1998, pp. 89.
33 在世纪史大家,乌尔曼是坚称王亦为神职人员的少数派,参见Walter Ullmann, The Growth of Papal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in the Ideological Relation of Clerical to Lay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3rd edition, 2010, pp. 402; 以及[英]沃尔特·厄尔曼世纪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第81页。
34 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 translated by J. E. Anderson Bloc, London Routledge, 1973, pp. 108109。译本参见[法]马克?布洛赫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北京商印书馆,2018,第160页。
35 顺便说明的是,后新教派系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Eucharist,天主教正教译圣体两个圣礼圣事,但神职人员须领受按立礼,信徒不能上祭台实施圣礼,也不能按立牧师。所以路德关于人人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思想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取消神职人员和信徒的所有区分。
36 哈特认为教会法根本就不是实证法,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294. 哈特这种态度反应了普通法系学者对教会法的无知和偏见是较普遍的。但如果哈特亲密圈子有人提醒他圣座不仅拥有主权和管辖范围,还有自己的独特政府理论,相信哈特一定会给出精彩分析,甚至可能会对其整个理论体系做出某种调整。
37 Berman, 1983, pp. 150.
38 Berman, 1983, pp. 215.
39 See Berman, 1983, pp. 239240.
40 分别参见Berman, 1983, pp. 215221, Corporation Law as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Church; Berman, 1983, pp. 237245, The Canon Law of Property.
41 教会社团法人最基层的单位是堂区,参见教会法典第515条第3款。我有些学者对这类社团的人合性质有所疑问,这是因为其属于世俗法理论已很少提及的非集体性noncollegial社团。在典型的教会社团,堂区教区神学为非集体性社团,而修会主教团则为集体性法人。非集体性社团是指重大事无需所有成员集体性参与,如堂区和教区事原则上即无须信徒参与,而主要是神职阶层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职人员相当于堂区和教区这类社团的积极成员,信徒则相当于消极成员,他们也因之各有不同的名册和档案建制性强的新教派系也有类似制度。教会社团法人的人合性质由此得到说明。而教堂则是具体教会社团的财,而不应设立为财团,否则教堂就会脱离与社团法人的法律关系,并须适用财团的治理方式,教会法当然不会有此规定。但我民总第92条第2款宗教事条例等却规定了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财团制度,这显然与教会法有较大冲突,需要协调。
42 历史地说,罗马主教在主教享有首席权,包括君士坦丁堡牧首宗主教Patriarch在内的部教长对此并无争议,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罗马主教及其代表在很多正式场合享有礼仪上的优先地位,罗马主教在普世教会的治权也在形式上被尊重实际上多通过技术手段加以屏蔽。但对部教会而言,所有主教都要由罗马主教任命的教宗制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首席权一词所涵盖的内涵。
43 Daniel Cenalmor, Jorge Miras, Il Diritto della Chiesa Corso di Diritto Canonico, traduzione di Eloisa Ballarò, Roma Edizioni Università della Santa Croce, 2005, pp. 203204.
44 马西利乌斯的代表作为其大卷和保卫者Defensor Pacis。英译本参见Marsilius of Padua, The Defender of the Peace, translated by A.S. Br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卷汉译本参见意马西利乌斯和的保卫者卷,殷冬水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伯尔曼也提及到了马西利乌斯的人民主权理论,参见Berman, 1983, pp. 275,但并没有提及他的圣秩权治权分离学说。
45 这个例子不具有典型性,宗座法对法官乃至律师有着极为严格的资质限制,仅教会法学和从业经验年限就使得执事很难进入法官行列,伯尔曼在其他地方明确说过宗座法法官为枢机主教和司铎,see Berman, 1983, pp. 209.
46 在伯尔曼看,格里高利改革本质上就是教皇革命。对这一看法学界是有争议的,美世纪史学家洛根F. Donald Logan, 1930就说伯尔曼的做法虽部分正确,但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distorts the historical reality,see Donald Logan,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06. 教皇革命这一概念更多是精英史观的物,伯尔曼也因此对那场宏大教会改革在目标的和阶段上的复杂性以及微观社会支持力量等因素缺乏应有重视,如修会的制度性强化和勃兴神职人员单身制度的大范围推广从主教推广到司铎教长选拔和神职晋升考核制度的改良性提升等。这些不仅影响到了他对教宗制度的分析,也影响到了该书第二卷对新教改革的处理,如没有解释为什么路德加尔文等要坚决取消修会神职单身制和主教制
47 后面会有提及,教宗是教会元首The pope was head of the church.的表述是有争议的。
48 Berman, 1983, pp. 206.
49 根据目前较权威的古典学检索网站perseus显示,plenitudo在武加大圣经使用较为普遍,就是丰富完整等较常见的表意,参见最后访问时间2019.5.13
50 美法史学者彭宁顿Ken Pennington, 1941认为1213世纪早期时,plena potestas与plenitudo potestatis最为接并经常混用,see J. H. Bur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 350C. 14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33. 布伦戴奇James A. Brundage, 1929就只使用plena potestas,认为它即为已足,see James A. Brundage, Medieval Canon Law,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116.
51 现有译本将该词译为了专制主义,并不精确。刘北成教授是较早坚持将absolutism译为绝对主义的学者,其说明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译者序,第3页。其更多说明可参见Berard L. Marthaler edi.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2nd edition, Vol. 1, Detroit Gale Group, 2003, pp. 44, absolutism.
52 有的学者把宗座的主权者身份与教皇元首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如乌尔曼,see Walter Ullman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apac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 2003, pp. 50, 59. 据此观点,1870年教皇被吞并之后宗座就不再拥有主权者身份。这种观念及其背后的家主权领土人民范式必须加以拒斥,宗座的主权主权者身份只是与圣座主权有关,而与教皇无关。
53 Berman, 1983, pp. 208.
54 参见教会法典,第113条第1款大公教会和宗座Apostolica Sedes因神意而成为法人。
55 美学者奥古斯丁Charles Augustine在1917年法典注释亦两次提及宗座和王座同为一人型社团法人,see Charles Augustine, A Commentary on the New Code of Canon Law, Vol. 2, St. Loius London B. Herder Book Co. 1922. p. 2. p.7. 有必要提及的是,教会法明确规定社团成员仅剩一人时,其法人人格不必然消灭,参见教会法典,第120条第2款若集体性法人成员仅剩一人之时,而该社团personarum universitas依其章程并未消灭的,则该成员有权行使社团之一切权利。
56 在我民法总则的起草和谈论过程,有学者认为一人公司或独资公司不符合社团的概念,进而反对社团财团分类作为法人的基本分类方法,其比较突出的参见梁慧星民法总则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暨南学报2016年01期,第24页。其对批判的观点参见罗昆我民法典法人基本类型模式选择,法学研究2016年04期,第133134页。
57 徐震宇博士将corporation sole译为单人合众体,将corporation译为合众体,这种处理使这些术语神秘化和复杂化了;相应地,将universitas译为体也同样有些让人困惑,universitas通常指社团,现多译为社团或团体,指财团时大多会加定语,如universitas rerum或universitas bonorum。相关翻译说明参见德内斯特·康托洛维茨王的两个身体世纪政治神学研究,徐震宇译,华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译后记,第731734页。
58 参见教会法典,第360条罗马教廷是最高宗座处理普世教会事之机构,其以宗座名义并依其权力而行使职能,为促进全教会利益而服;其包含即教宗秘书处公事委员会各圣部各宗座法以及其他机构。
59 Berman, 1983, pp. 207.
60 Berman, 1983, pp. 214.
61 Berman, 1983, pp. 215.
62 法菲利普·内莫教会法与神圣罗马帝的兴衰世纪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上海华师大出版社,2010,第 242243页。
63 李筠论西方世纪王权观现代家权力的世纪起源,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第161页。
64 佀化强体的起源构造和选择西暗合与差异,法学研究2016年05期,第175页。该文章线索是有机体学说,家作为政治有机体只能存在一个头部元首,这是对的,但若因此认为王座宗座并存是双首怪物则是不恰当的,教会与家不是同一维度内的有机体。
65 根据圣经教理和教会法,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宗座严格说只是最高权威supreme authority,但人们可以说宗座称是教会的有形元首visible head,see John P. Beal, James A. Coriden, Thomas J. Green edited, New Commentary on the Code of Canon Law, Study editio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0, pp. 490; Ern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94.
66 这种理论可以追溯到世纪的但丁马西利乌斯等人,他们所持有的家观本质上是罗马帝式的,即教会诞生于罗马帝之,因而只是家权威之下的宗教团体,没有自己的主权和独立于政府的管辖领域。
原文载于清华法治论衡第28辑。